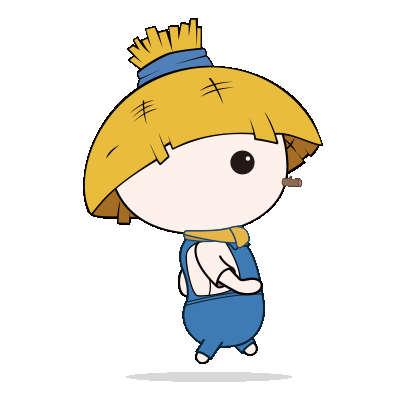将春夜燃尽
第63章 亲爱的那只是一场幻觉(……(第1/2页)
“你这样, 叫我怎么下得来台呢。”
盛鲸挣脱他的钳制,倒退几步瘫软在另一个单人沙发里,蜷缩着默默流泪。
靳言追过去, 非要跟她坐一块儿,摆出一副油盐不进的模样, 说着强词夺理的话:“换一个曲目而已, 又不是不让你去。”
盛鲸气得发抖,浑身的尖刺都竖了起来, 推开他:“我已经说了,不能换!换不了!”
靳言被推得一个踉跄, 笑了笑,随意地坐到她旁边。但笑容毫无暖意,眼底一片冰凉,语气更是冷淡至极:“既然你已作出选择, 那自己把衣服了tuo坐上来。”
近乎羞辱的命令。盛鲸不哭了, 冷脸瞪他,反唇相讥:“你疯够了么?”
他夹着烟, 声音喑沉,目光如冷锐的刀划过:“呵, 现在嫌弃我了?被我操的时候怎么叫得那么热情。”
盛鲸不甘示弱:“不就是活丨塞运动吗,说不定震丨动bang能让我更热情。”
言下之意, 他还不如震丨动bang。
靳言仿佛听见什么笑话似的,哑然失笑:“呵――”
声音听起来平静、淡然,似乎和往常没说笑没什么区别。可实际上,他整个人是紧绷着的,沉郁的表情蕴藉着薄怒。
对峙了一会儿。
盛鲸自顾自地掏出口红,对着手机补了补妆容, 然后站起身冷冷地说,“我走了。”
眼看着时间越来越近,再不走就要被迫缺席交违约金了。
她舍不得那笔钱。
没走几步,靳言伸手将人一把拉回,钳着她手腕面无表情地质问:“走哪儿去?我同意了吗?”
盛鲸瞥他一眼,狠下心来,“你放开我。和别人上过床的不是我,是你。”
靳言脸上一下子失了血色,颓然地松开她:“叫司机送你。”
“不用。”盛鲸头也不回地出了门。
*
盛鲸走后,靳言几次摸索着想站起身。
但他耳畔灌满来自四面八方的、歇斯底里的渗人笑声,将他钉在原地,浑身僵硬,连撑着沙发都手抖,被迫靠着椅背剧烈地喘气,根本起不来。
眼前浮现一张美丽而狰狞的脸,泛着苍白的死气――那是他最熟悉的噩梦。
“嘻嘻嘻,我早说了,你就是一个没人要的讨嫌鬼。”
“你怎么脸皮那么厚?我说让你滚远点。”
“你活着,就是耻辱。”
“你为什么不去死。”
靳言不能说话,不能动。眼睁睁地看着它逼近,停在眼前,血流成河,然后目龇尽裂地扑上来,揪住他的衣领、扼住他的喉咙,拖着他暴走,喋喋不休地狂言:
“你看过无数次凌晨三点的夜空,你知道四点的第几分钟开始天亮。
你了解帕罗西汀甚于阿司匹林。
你俯视深渊,清醒地看着自己坠入噩梦。
你总是听见午夜有人在窗台唱歌欢笑。
你一遍一遍地鼓励自己,可你还是觉得自己是个错误。
他们说你是天之骄子,这真好笑,午夜梦回,你时常为此痉挛、惊厥。
你需要需要一遍一遍鼓励自己,才敢试图去喜欢一个人。
然而,亲爱的那只是一场幻觉,没有人可以得到救赎,请跟我一起乘风而去。”
靳言动了动嘴皮子,不,您说的不对。我不是耻辱,我不是错误,有人爱我的。
它环顾四周,似是疑惑,似是不解:“可是这儿一个人也没有,谁会来爱你呢?谁能来爱你呢?”
“她。”
“她已经走了。她和你妈一样抛弃了你!”它死死地卡住他的喉管,令他几乎窒息,“你活得那么痛苦,为什么还不去死呢?”
它满口鲜血,还要桀桀而笑,“还不认命么?你们这种人,早就该死了。”
靳言的眼神失去了光亮和波澜:是啊。为什么我还活着。
见状,它满意地引诱着:“你好好考虑,死了什么痛苦也没有。”
它忽然褪去满身戾气,变回年轻时温柔骄矜的模样,“妈妈在下面等你,只要你死了,妈妈就再也不打你不骂你了。妈妈会爱你。”
靳言放弃了挣扎,眼神涣散:“真的么?”
“真的。”
*
某高端汽车品牌宣传活动。
“接下来,热烈欢迎北城剧院主要演员,茱莉亚歌剧系的艺术家盛鲸小姐,为我们带来奥芬巴赫轻歌剧《木偶之歌》。”
轻歌剧于十九世纪成为独立歌剧体裁。它是一种浪漫多愁善感、情节曲折的小歌剧,以通俗的诙谐轻喜剧形式来表演。
主持人报幕后,盛鲸轻提裙摆飞奔到舞台中央,然后行了一个优雅而僵硬的蹲礼,看起来完全是真人版的木偶小姐。
其实,这个动作这不是原本的出场方式。前几日在剧院设计的出场方式,是被男演员向扛木偶那样,扛着